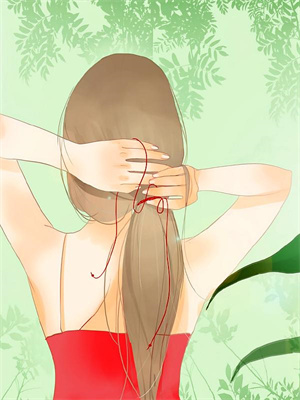简介
喜欢历史脑洞小说的你,有没有读过“留不住就算了”的这本《重生崇祯八年》?本书以刘寅为主角,讲述了一个充满奇幻与冒险的故事。目前小说已经连载,精彩内容不容错过!
重生崇祯八年小说章节免费试读
第一节 苏醒
刺鼻的恶臭钻进鼻腔。
不是实验室里化学试剂的酸味,也不是图书馆旧书纸张的霉味,而是一种混合了粪便、腐肉和汗垢的,属于彻底绝望的气味。
刘寅猛地睁开眼。
天空是铅灰色的,几片破絮般的云低垂着,像是随时要压下来。视线所及之处,是布满蛛网的朽木房梁,瓦片残破,露出一个个不规则的窟窿。冷风从那些窟窿里灌进来,带着三月初春的寒意,刮在他脸上。
他躺在一堆干草上。
不,不是干草。
刘寅艰难地侧过头,看见身下压着的,是早已枯黄发黑的麦秸,混杂着不知名的杂草。几根细枝戳着他的腰侧,疼痛如此真实。
这是哪里?
他最后的记忆停留在图书馆四楼的古籍阅览室。桌上摊开的是《崇祯实录》第八卷的影印本,旁边笔记本上写着:“崇祯八年,陕西北起榆林延安,南至西安汉中,赤地千里,人相食…”
然后呢?
然后窗外雷声轰鸣,暴雨将至。他记得自己起身去关窗,一道刺目的白光——
头痛欲裂。
刘寅挣扎着坐起来,这个简单的动作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。身体虚弱得可怕,胃部传来剧烈的抽搐感,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饥饿。他低头看自己的手,骨节突出,皮肤蜡黄,指甲缝里塞满了黑色的污垢。
这不是他的手。
他在实验室里操作精密仪器的手,握笔书写论文的手,应该是干净、修长、指甲修剪整齐的。
而这双手,粗糙,皲裂,布满冻疮和茧子。
“我…穿越了?”
这个念头荒谬得让他想笑,但喉咙干得发不出声音。他环顾四周——这是一座破败的庙宇,神像早已倒塌,只剩下半截泥塑的躯干倒在墙角,彩绘剥落,露出里面的稻草和木架。
庙里不止他一个人。
几十个人,或许上百,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。大多蜷缩着,用破布或草席裹着身体。空气中弥漫着死寂,只有偶尔传来的咳嗽声和婴儿微弱的啼哭,证明这里还有活物。
刘寅的目光扫过离他最近的一个身影。
那是个老人,侧躺着,眼睛半睁着,但瞳孔已经涣散。一只苍蝇落在他干裂的嘴唇上,他毫无反应。
死了。
这个认知让刘寅的胃一阵抽搐。他强迫自己移开视线,却在另一处看到了更可怕的景象——墙角,两个瘦得皮包骨的人,正围着一具刚断气的尸体,用石片切割着什么。
人相食。
笔记本上的三个字,此刻变成了眼前的现实。
刘寅猛地捂住嘴,强烈的恶心感涌上来。他干呕了几声,却只吐出一点酸水。胃里早就空了。
冷静。必须冷静。
他深吸一口气——尽管污浊的空气让他作呕——开始梳理现状。
第一,他穿越了,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,来到了某个古代时空。
第二,从庙宇的建筑风格、人们的衣着(那些破烂但能看出形制的衣衫),以及“人相食”的惨状推断,很可能就是明末。
第三,最坏的情况是,他穿越到了饥荒最严重的地区,而且附身在了一个快要饿死的流民身上。
第四,如果他不想成为墙角那堆被切割的肉,就必须立刻找到食物和水。
知识。他唯一的优势就是知识。历史知识,科学知识,生存知识。
刘寅努力回忆关于明末饥荒的资料。崇祯八年,1635年。陕西大旱,蝗灾,朝廷加征“辽饷”、“剿饷”,官吏层层盘剥,农民先是卖儿卖女,然后吃树皮草根,最后…
他的目光落在自己破烂的衣衫上。这是一件深灰色的短褐,粗麻质地,早已磨得发亮,袖口和衣襟处打着歪歪扭扭的补丁。腰间束着一根草绳,挂着一个瘪瘪的布袋。
他摸索着布袋,里面空空如也。
但当他摸向腰间另一侧时,手指触到了几个硬物。
刘寅的心跳加速了。他小心翼翼地将那几个东西掏出来,借着庙宇破洞透下的微光查看。
一个银色的小方块——他的Zippo打火机。上面刻着毕业时导师送的寄语:“以史为鉴”。
一把莱泽曼多功能工具钳。
一本用防水材料包裹的笔记本,封皮上印着“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札记”。
还有一支圆珠笔。
这几样东西,在图书馆停电时他常备在随身小包里,此刻却成了他在这个时代最珍贵的宝物。
泪水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。不是悲伤,而是一种荒诞至极的冲击。这些现代工业的产物,在这个饿殍遍野的破庙里,显得如此格格不入,又如此珍贵。
他迅速将东西塞回衣服内衬——那里有个破口,刚好可以藏匿。绝不能被人看见。
就在这时,庙门口传来一阵骚动。
第二节 张彤
几个身影踉跄着走进来,挡住了门口本就微弱的光线。
为首的是个三十来岁的汉子,身材高大,但瘦得颧骨高耸。他穿着一件破损的鸳鸯战袄,红色早已褪成污褐色,胸口的“兵”字补子只剩下一半。左臂用脏布条胡乱包扎着,渗出血迹。
他身后跟着四五个人,有男有女,都面黄肌瘦,眼神麻木。
“就这里吧,歇口气。”穿战袄的汉子声音沙哑,在庙里扫视一圈,目光在墙角那两人身上停留片刻,眉头紧皱,但没说什么。他找了个相对干净的角落,扶着墙慢慢坐下。
刘寅注意到,这汉子虽然虚弱,但坐姿依然带着一种军人的习惯——背脊挺直,目光警惕地扫视四周。他的右手始终按在腰间,那里挂着一把没有鞘的腰刀,刀身锈迹斑斑,但刃口隐约还能反光。
明军士兵?逃兵?还是溃兵?
刘寅心中快速分析。崇祯年间,军队欠饷严重,士兵逃亡或哗变是常事。这人带着伤,又和一群流民在一起,很可能是脱离了建制。
或许是刘寅观察的目光太明显,那汉子突然转过头,视线和他对上。
那是一双深陷的眼睛,布满血丝,但瞳孔深处还残留着一点锐利的光。
“看什么?”汉子冷冷道。
刘寅心里一紧,连忙移开目光,低下头。在这个秩序崩坏的环境里,任何不必要的注意都可能招来祸患。
但已经晚了。
汉子站起身,拖着伤腿,一步步走到刘寅面前。刘寅能闻到他身上浓重的血腥味和汗臭味。
“新来的?”汉子问,“哪儿的人?”
刘寅张了张嘴,喉咙干涩得发不出完整的声音:“…西安…府。”
他故意含糊了地点。实际上,这具身体的记忆碎片正在一点点涌入——原主也叫刘寅,是个童生,家在西安府郊县,父母在去年饿死了,他跟着流民队伍向东走,想去河南找远亲,结果倒在半路。
“识字的?”汉子挑了挑眉,似乎有些意外。他蹲下身,仔细打量着刘寅,“像个读书人。怎么混成这样?”
刘寅没回答,只是指了指自己的喉咙,做出喝水的动作。
汉子盯着他看了几秒,突然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皮囊,拔掉塞子,递过来。
水。
浑浊的,带着土腥味的水。
但对此刻的刘寅来说,这就是琼浆玉液。他接过来,小心地喝了一小口,润湿喉咙,然后强迫自己只再喝两口,就还给对方。
“多谢…军爷。”他哑着嗓子说。
“军爷?”汉子嗤笑一声,“早不是了。姓张,张彤。以前在榆林镇当个小旗,现在…呵,就是个等死的。”
他接过水囊,自己却没喝,而是走回角落,递给一个蜷缩着的女人。那女人怀里抱着个孩子,孩子的小脸通红,呼吸急促。
“翠儿,给娃喂点水。”张彤说。
女人木然地接过,小心地往孩子嘴里滴了几滴。孩子咂了咂嘴,发出微弱的哭声。
刘寅的视线落在那个孩子身上。看体型,不过两三岁,此刻紧闭着眼,额头有明显的汗珠,呼吸时胸腔起伏剧烈。
肺炎?还是伤寒?
无论是哪种,在这个没有抗生素的时代,对营养不良的幼儿来说都是致命的。
张彤坐在女人身边,看着孩子,脸上的表情是深沉的疲惫和无奈。他伸手摸了摸孩子的额头,烫得吓人。
“烧得更厉害了。”他低声说。
女人终于有了反应,眼泪无声地流下来:“当家的…娃他…他是不是…”
“别胡说!”张彤打断她,但声音里没有多少底气。
刘寅的心脏砰砰直跳。一个念头在脑中疯狂生长:这是一个机会。展示价值的机会。获取信任的机会。
但风险也同样巨大。如果他判断错误,或者方法无效,可能会立刻被愤怒的张彤打死。
然而,继续躺在这里等死,结局也不会更好。
他深吸一口气,撑着虚弱的身体,摇摇晃晃地站起来,朝张彤那边走去。
庙里其他流民漠然地看着,没人关心他要做什么。只有墙角那两个切割尸体的人,抬头瞥了一眼,眼神空洞。
“张…张兄。”刘寅走到近前,保持着一米左右的距离——这是不引发警惕的安全距离。
张彤抬起头,眼神锐利:“什么事?”
“孩子…是发热?”刘寅问。
张彤没说话,只是盯着他。
“我…略懂一点医术。”刘寅谨慎地选择措辞,“或许…可以试试。”
“你是郎中?”张彤身后的一个年轻男人怀疑地问。他看起来二十出头,虽然瘦,但眼神比其他人灵动些。
“不是正经郎中,”刘寅摇头,“但读过几本医书,家里…以前开过药铺。”他编造了一个合理的背景。
张彤沉默了片刻。孩子又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,小脸憋得发紫。
“你试试。”张彤最终说,声音沙哑,“但若害了我儿…”
他没说完,但眼神里的警告意味很明显。
刘寅点点头,小心翼翼地在女人身边蹲下。他先观察孩子的症状:高热、咳嗽、呼吸急促、脸颊潮红。他轻轻扒开孩子的眼皮——眼结膜充血。又听了听呼吸音——有轻微的啰音。
肺炎的可能性很大。
“有清水吗?干净的布?”刘寅问。
张彤从行囊里翻出一块相对干净的麻布,又递过水囊。刘寅接过,却没有直接用。他记得水囊里的水是浑浊的。
“需要烧开的水。”他说。
“烧开?”年轻男人皱眉,“这时候哪去找柴火烧水?”
刘寅指向庙外:“刚才进来时,我看到外面有些枯枝。庙里应该有破木头。”他顿了顿,“另外,我需要盐。”
“盐?”张彤的眉头拧紧了,“你小子是不是耍我?盐比命还金贵,我哪有盐?”
刘寅从怀里——实际上是内衬里——摸出那个Zippo打火机。他背对着其他人,用身体挡住动作,啪的一声打燃。
一小簇火焰跳了出来。
张彤和他的同伴都愣住了,眼睛瞪大。
“这是…”年轻男人凑近了些。
“西洋火折子。”刘寅迅速编了个理由,“我家传的。”他不能让这些人知道这东西的真正来历,“用这个生火,费不了多少柴。至于盐…”
他看向庙宇角落。那里墙根处,有白色结晶物渗出——硝石。明代建筑,尤其是庙宇、厕所等地方,墙壁常因有机物分解产生硝酸盐,这是制作黑火药的原料之一,但也能通过简单提纯获得…虽然不是食盐,但可以制造消毒盐水。
“那不是盐。”张彤顺着他的目光看去,“那是墙硝,苦的,不能吃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刘寅说,“但我有办法让它有用。”
他看向张彤:“张兄,信我一次。若不成,随你处置。”
张彤盯着他手中的打火机,又看了看怀里气息越来越微弱的孩子,最终咬了咬牙。
“洪国玉,”他对那个年轻男人说,“去捡柴。翠儿,你照顾孩子。”然后他看向刘寅,“你要墙硝?我给你刮下来。但你最好真有用。”
第三节 净水与盐水
半个时辰后,庙宇中央升起了一小堆火。
火是用刘寅的“西洋火折子”点燃的,这神奇的一幕让庙里还醒着的流民都投来目光。但饥饿和疲惫让他们没有力气好奇,大多数人只是看了一眼,又蜷缩回去。
张彤用腰刀的刀背,从墙角刮下了一层白色的墙硝结晶。刘寅则指挥洪国玉——那个年轻男人——用破瓦罐从庙后的水坑里打了水。
水是浑浊的黄绿色,漂浮着杂质。
“这水不能喝,会拉肚子,死得更快。”洪国玉说。
“所以要煮开。”刘寅将瓦罐架在几块石头上,悬在火堆上方。火焰舔着罐底,很快,水开始冒泡。
等待水开的时间,刘寅开始处理墙硝。他将刮下的白色晶体放在一块相对平坦的石板上,用另一块石头小心研磨。这不是食盐(氯化钠),主要是硝酸钾,还有硝酸钠、硝酸钙等杂质。直接吃有毒,但…
水开了。
刘寅让洪国玉将瓦罐移开,稍微冷却。然后他撕下一小块麻布,叠成四层,做成简易过滤器。他将开水慢慢倒过布层,滤掉大部分悬浮物。
得到的水虽然还不是清澈的,但已经好多了。
接下来是关键一步。刘寅取了一小撮研磨好的墙硝粉末,投入过滤后的热水中,搅拌溶解。硝酸钾溶解度随温度变化大,热水能溶解更多,冷却后会析出较纯的晶体。但他不需要纯化,他需要的是…硝酸钾溶液的消毒作用。
严格来说,这不是生理盐水(0.9%氯化钠),高浓度的硝酸钾溶液甚至对组织有刺激性。但刘寅记得,硝酸钾溶液有一定的抗菌效果,而且钾离子对高热脱水患儿可能有微弱的电解质补充作用——当然,风险很大。
但他别无选择。
“张兄,”刘寅捧着瓦罐,对张彤说,“这水不能喝,但可以给孩子擦身降温。另外,我需要干净的布,蘸这水,轻轻擦他的嘴唇和口腔内侧。”
他不敢内服,只能外用。物理降温加上可能的局部抗菌,是他能想到的极限。
张彤盯着瓦罐里微浑的液体,又看了看怀里奄奄一息的孩子。
“你确定?”
“不确定。”刘寅诚实地回答,“但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。孩子高热不退,再这样下去…”
张彤的脸颊肌肉抽动了一下。他看向妻子翠儿,女人已经哭干了眼泪,只是死死抱着孩子。
“试。”张彤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。
刘寅松了一口气。他指导翠儿用布蘸着微温的硝酸钾溶液,轻轻擦拭孩子的额头、腋下、脖颈。然后用另一小块干净布,蘸湿后小心地擦拭孩子的口腔。
孩子起初挣扎了一下,但很快又陷入昏睡。
整个过程,庙里静悄悄的。只有火堆燃烧的噼啪声,和远处偶尔传来的呜咽风声。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。
大约过了一炷香时间,洪国玉突然低呼一声:“好像…呼吸平稳些了?”
刘寅凑近观察。孩子的脸色依然潮红,但呼吸的急促程度似乎略有缓解。最明显的是,他不再剧烈咳嗽了。
张彤伸手探了探孩子的额头,虽然还是烫,但好像没有之前那种灼手的感觉了。
“有效…”他抬起头,看向刘寅,眼神复杂,“你…真的懂医?”
“只是碰巧知道这个土方。”刘寅谦逊地说。他不敢居功,实际上,他也不知道是硝酸钾溶液起了作用,还是物理降温的效果,或者孩子只是暂时缓解。
但无论如何,孩子的情况似乎稳住了。
张彤深深看了刘寅一眼,然后从怀里摸出半块黑乎乎的东西,递了过来。
“吃。”
刘寅愣了一下,接过来。是块杂粮饼,硬得像石头,表面长着霉点。但对此刻的他来说,这是无上美味。
他小口小口地咬着,用唾液慢慢润湿,艰难地咽下去。胃部因为食物的进入而剧烈收缩,带来一阵疼痛,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活过来的感觉。
“谢…谢谢张兄。”他含糊地说。
张彤摆摆手,目光又回到孩子身上。翠儿还在不停地用布蘸水擦拭。
洪国玉凑到刘寅身边坐下,压低声音:“兄弟,你真行啊。那西洋火折子,还有那墙硝的用法…你到底是干什么的?”
刘寅一边嚼着饼,一边快速思考如何回答。洪国玉看起来是这群人里最有脑子的,不好糊弄。
“家里以前开药铺,也做些杂货生意,接触过西洋人。”刘寅半真半假地说,“后来…遭了灾,什么都没了。”
这是明末流民的标准故事,不会引人怀疑。
洪国玉点点头,没再追问,只是看着火堆出神。过了一会儿,他说:“张大哥是好人。他本可以不救我们,自己走的。他武艺好,又有刀,一个人活下来的机会更大。”
“你们怎么遇到的?”刘寅问。
“在延水关附近。官军溃散了,张大哥受了伤,我们几个是同村的,一起逃难。”洪国玉苦笑,“一开始有二十多人,现在…就剩这几个了。”
刘寅默默听着。他想起史书记载,崇祯八年,陕西巡抚练国事调兵围剿流寇,但官兵饥疲,多有溃散。张彤很可能就是那时脱离队伍的。
“接下来打算去哪?”刘寅问。
洪国玉摇头:“不知道。往东走?听说河南那边年景好些。但这一路…你也看到了。”
他看向庙里横七竖八的人,眼神黯淡。
刘寅也沉默下来。他的大脑在飞速运转。跟着张彤这群人,暂时安全有了保障,张彤看起来讲义气,而且有武力。但长远呢?继续漫无目的地流浪,最终可能还是饿死,或者被其他流民团体、土匪、甚至官兵杀死。
必须有个计划。
必须找到根据地,生产食物,建立秩序。
但这个想法太疯狂了。他现在只是一个刚捡回半条命的流民,凭什么?
知识。只有知识。
“洪兄弟,”刘寅压低声音,“你读过书?”
洪国玉愣了一下:“识几个字,以前在村里跟老童生学过。怎么?”
“如果…我是说如果,”刘寅斟酌着词句,“我们能找到一个地方,有水源,能开荒种地,还能找到些…别的东西,比如铁矿、煤矿,你觉得我们能活下去吗?”
洪国玉转过头,认真地看着刘寅,像是第一次认识他。
“铁矿?煤矿?”他笑了,笑容里带着苦涩,“兄弟,你想太远了。现在只要能找到一口吃的,不被饿死,就是老天开眼了。”
“但只是找吃的,永远吃不饱。”刘寅坚持道,“今天找到一点,明天呢?后天呢?我们必须能自己生产。”
洪国玉不笑了。他盯着刘寅看了很久。
“你…不像普通流民。”他慢慢说。
刘寅心里一紧。
“我读过一点书,知道些道理。”洪国玉继续说,“你说得对,光靠乞讨、抢掠,活不长。但开荒种地需要种子、农具、时间,还要官府不下发文书赶人…太难了。”
“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偏僻的,官府管不到的地方。”刘寅说,“比如…山里。”
洪国玉眼睛一亮,但随即又黯淡:“山里土匪多。”
“土匪也是人,也要吃饭。”刘寅说,“我们可以…”
他的话被打断了。
庙门口,又进来了几个人。
第四节 抉择
这次进来的是三个男人,都拿着棍棒,为首的是个满脸横肉的壮汉,虽然也瘦,但比庙里大多数流民强壮得多。他一进来就扫视全场,目光最终落在火堆上。
“哟,还有火?”壮汉咧嘴笑了,露出黄黑的牙齿,“挺会享受啊。”
张彤缓缓站起身,手按在了腰刀上。洪国玉和其他几个男人也警惕地站起来,围在火堆旁。
刘寅注意到,张彤这边能战斗的,包括张彤自己,只有四个成年男子,其他都是老弱妇孺。而对方三个,看起来都是青壮。
“这庙不是谁家的,我们生火,关你什么事?”洪国玉说,声音尽量平静。
“是不关我事。”壮汉慢悠悠地走近,“但爷们几个饿了,看你们还有火,想必有点吃的吧?拿出来,分分。”
这是明抢。
庙里其他流民都缩紧了身体,不敢出声。墙角那两个切割尸体的人,也停下了动作,警惕地看着这边。
张彤往前跨了一步,挡在妻子和孩子前面。
“没有吃的。”他声音不高,但带着军人的冷硬,“要拼命,奉陪。”
壮汉打量了一下张彤身上的旧战袄和腰刀,眼神闪过一丝忌惮,但看到张彤包扎的左臂,又有了底气。
“兄弟,别逞强。你受伤了,动起手来,谁死谁活还不一定。”壮汉说,“我们只要吃的,不想见血。”
气氛骤然紧张。
刘寅的大脑飞快转动。硬拼,张彤这边未必输,但肯定会有伤亡。而且一旦受伤,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,很可能就是死路一条。
必须避免冲突。
“这位好汉,”刘寅突然开口,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。他强作镇定,站起身,对壮汉拱了拱手,“吃的,我们确实没有。但我知道哪里可能有。”
壮汉狐疑地看着他:“哪里?”
“西边,进山的路。”刘寅说,“我来时路过,看到有些野枣树,虽然现在没果,但树皮和根可以充饥。另外,山里可能有野物。”
“放屁!”壮汉身后一个瘦高个骂道,“山里有土匪,去了就是送死!”
“正是因为土匪在,官府不去,野物才多。”刘寅坚持道,“而且,我知道一个地方,以前是猎户的落脚点,有废弃的窝棚,可以遮风避雨。”
他在赌。赌这具身体原主的记忆碎片——原主似乎确实在山里待过几天。
壮汉盯着刘寅,似乎在判断他话的真假。
“你带路?”壮汉问。
刘寅看了一眼张彤。张彤眉头紧锁,但微微点了点头。
“我带路。”刘寅说,“但有个条件。”
“说。”
“我们这些人一起。”刘寅指了指张彤一伙,“要活一起活,要走一起走。”
壮汉笑了,笑容狰狞:“小子,你以为你有资格谈条件?”
“我有。”刘寅从怀里掏出Zippo打火机,啪的打燃,“我有这个,可以生火。山里晚上冷,没火会冻死。我还能找水,识路。杀了我,你们进山也是死路一条。”
火焰在昏暗的庙里跳动,映着壮汉惊疑不定的脸。这个“西洋火折子”显然超出了他的认知。
“妈的,邪门…”壮汉啐了一口,但眼神里的贪婪掩饰不住。他想要这个神奇的火折子。
“好,一起走。”壮汉最终说,“但进了山,你得听我的。还有,这火折子,得给我。”
“到了落脚点,可以借你用。”刘寅寸步不让,“但现在不行。”
壮汉脸色一沉,但看了看张彤手里的刀,又看了看火折子,最终哼了一声:“行。天亮就走。”
他带着两个手下,到庙的另一角坐下,但眼睛一直盯着这边。
危机暂时解除,但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。
张彤拉着刘寅坐下,压低声音:“你真知道山里有个落脚点?”
“大概知道方向。”刘寅如实说,“原…我以前在山里躲过几天。”
张彤盯着他:“为什么帮他们?他们摆明了不怀好意。”
“因为我们人少,需要壮劳力。”刘寅冷静地分析,“开荒、建房、防御,都需要人手。他们虽然危险,但也是力量。关键在于,我们能否控制住。”
张彤眯起眼:“控制?”
“张兄,你有刀,有武艺,有带兵的经验。”刘寅说,“我有…一些特别的知识。我们合作,也许真能在山里活下去。但首先,我们需要人。”
洪国玉在一旁听着,眼神闪烁:“刘兄弟,你…到底想做什么?”
刘寅看着跳动的火焰,沉默了几秒。
“我想活下去。”他慢慢说,“不是像狗一样苟延残喘地活,而是像人一样,有尊严,有希望地活下去。我想建一个地方,让跟着我的人都能吃饱饭,不受欺负。”
他抬起眼,看向张彤和洪国玉:“就我们几个,做不到。我们需要更多人,需要规矩,需要组织。山里,可能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”
张彤和洪国玉都沉默了。火光照着他们瘦削而肮脏的脸,表情复杂。
“你像个说书的。”张彤最终说,但语气里没有嘲讽,只有深深的疲惫和一丝…动摇。
“也许吧。”刘寅笑了笑,“但张兄,你难道想一直这样流浪,直到某天饿死在路边,或者被人像畜生一样宰了吃肉?”
张彤的手猛地握紧了刀柄。
“不想。”他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。
“那就试试。”刘寅说,“最坏的结果,不过是死在山里。但至少,我们是拿着武器,为了活命而战死,不是像现在这样等死。”
长久的沉默。
庙外,风声呜咽。远处隐约传来狼嚎。
“好。”张彤最终说,“我跟你赌一把。但有一条——进了山,如果那三个人敢动手,我会先杀了他们。”
“同意。”刘寅点头。
洪国玉叹了口气,又笑了:“反正也是死路一条,不如跟你们疯一把。刘兄弟,我叫洪国玉,以后…听你吩咐了。”
“不是听我吩咐。”刘寅摇头,“是我们一起,商量着来。”
他看向火堆,又看向庙外深沉的夜色。崇祯八年的陕西,饿殍遍野,烽烟四起。而他,一个来自未来的灵魂,即将带着这群绝望的人,走进秦岭的群山之中。
前路未知,生死未卜。
但至少,他们有了一个方向。
刘寅摸了摸内衬里的笔记本和工具钳。这些来自未来的知识,将是他唯一的武器。
他闭上眼,开始回忆秦岭的地理特征、矿产资源分布、这个时代的农作物种类…
第一步,活下去。
第二步,找到根据地。
第三步…
他的思绪被孩子的咳嗽声打断。翠儿惊喜地小声说:“当家的,娃醒了,要喝水!”
张彤急忙凑过去。孩子睁开了眼,虽然还是很虚弱,但眼神有了焦点。
刘寅松了一口气。至少,他救下了一条命。
这是个开始。
天快亮时,刘寅靠在墙角假寐。他听到张彤和洪国玉在低声商量进山的路线,听到那三个壮汉粗重的呼吸声,听到庙里其他流民梦中痛苦的呻吟。
他悄悄拿出笔记本和圆珠笔——圆珠笔在这个时代不会引起怀疑,可以伪装成炭笔——在空白页上写下:
崇祯八年三月十八日(推测)
位置:西安府以东,具体不明
状态:极度饥饿,虚弱
团队成员:张彤(前明军小旗,伤)、洪国玉(识字的流民)、翠儿(张妻)、病童(名未知)、其他老弱四名
潜在威胁:壮汉三人组(需警惕)
目标:进入秦岭,寻找根据地
首要任务:1.找到稳定水源 2.获取食物 3.建立基本防御
长期规划:开荒、冶铁、建立秩序
备注:现代物品剩余:Zippo打火机、莱泽曼工具钳、笔记本、笔。必须谨慎使用。
写完,他将笔记本塞回内衬,抬头看向庙门。
天色微明,一缕惨白的光从破洞照进来。
新的一天,开始了。
也是他在这个黑暗时代,挣扎求生的第一天。
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,不知道这个简陋的团队能走多远,不知道历史是否会因他而改变。
他只知道,他必须活下去。
为了自己,也为了这些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人。
“都醒醒,”张彤站起身,声音恢复了军人的干脆,“收拾一下,准备进山。”
庙里,人们开始缓慢地、艰难地移动。
刘寅深吸一口气,站了起来。
走向群山,走向未知,走向或许有一线生机的未来。
崇祯八年,他的故事,才刚刚开始。

 维C文学
维C文学